-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八)意必吉祥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七)宗教神仙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六)世俗百态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五)仕女婴戏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四)肄武绥藩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三)锐意文治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二)山水寄情
- 黄斐: 康熙瓷器人物纹及其文化内涵探析 (一) 耕织牧渔
5. 仕女婴戏 循守宗法伦常
仕女画入瓷早可见于唐代长沙窑,至明末清初进入繁盛,尤以康熙时期的评价最高。《陶雅》曰:“瓷器最重画工,雍正以花卉最工,人物则不及康熙远甚,尤以画美人之瓶罐,不能见重于后世。”故宫博物院藏青花仕女图盘[图37–39],盘心分别刻画了女子逗弄鹦鹉、拈线刺绣和执笔绘兰的生活情态,画中女子眉清目秀,温柔典雅。为突出主体人物,除山石、案几、寥寥片叶外,几无其他陪衬,人物简约凝练,极具艺术个性。这样独特的创作审美,仅在康熙朝被推崇并传播,这是对明末以来,从本心出发,弃“矩”求“理”的社会思潮的延续,也有赖于当时满汉中西文化的碰撞和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



多人仕女图主要以拈花、庭院赏游、舞蹈宴乐为主[图40-44],背景多为庭院景致。古代女子居内,“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庭院在建筑内部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较为安静的室外活动空间,园中亭台楼榭、洞石花木,清幽雅致,是中上阶层女性消遣寂寞的重要场所,也代表了男权为主的封建社会对理想女性生活的审美倾向。





古代女性在家庭中主要担负抚育、教养后代的职责,故仕女往往与婴孩相伴,称为“仕女婴戏图”[图45-46]。端庄、恬静的女性陪伴着纯真可爱、活泼俏皮的孩童,动静相宜,充满和谐生动的生活意趣,也寄托了家庭和睦、子孙兴旺的美好愿望。明末清初,战乱频繁,人口锐减。为鼓励生育,康熙五十一年(1712)颁发谕旨:“令直隶督、抚将今钱粮册内有各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永为定数,免其加增钱粮,续生人丁,永不加赋。”在政府的倡导下,瓷绘婴戏图[图47]的发展也再次进入繁盛期。举莲、攀花、打鼓、斗草、蹴鞠、放纸鸢、持灯笼、骑竹马等程式皆可入画。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青花“四妃十六子图”罐[图48],寓人丁兴旺、子孙多贤。康熙青花百子图四足方花盆[图49],以更宏大、热烈、欢腾的百子婴戏累加祥瑞,祈福国祚,烘托出喜庆吉祥的气氛。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婴童的形象不仅具有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更融合了天人合一思想、宗教信仰和宗法伦常。道教对婴儿持极高的评价和赞美。老子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婴儿少私寡欲,纯真自然,启发人对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哲学思虑。瓷器喜绘婴童举莲,这一形象与佛教经典联系密切。《佛说阿弥陀佛经》载:“化生童子本无情,尽向莲花朵里生,七宝池中洗尘垢,自然清净是修行。”随着佛教的本土化,化生童子在宋代衍生出手持荷花,象征生殖繁衍的七夕节物摩喉罗,并进一步演化为小童围肚兜,坐于莲上或一手举莲的形象,寓意“连生贵子”。

图48 青花“四妃十六子”图罐



儒家视生育为家庭稳定、宗族延续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不仅提倡多生,更鼓励追求事功,即学而优则仕。体现在瓷器上,常见“五子登科”“蟾宫折桂”等题材。当然,中国传统文化不仅重视“生”,更以“仁”为内核,融入仁爱、孝悌等伦理观念,为生育教养、文明教化和家族延续提供了保障。故宫博物院藏康熙青花开光人物图钵式炉[图50],绘“二十四孝图”,正是这一文化观念的有力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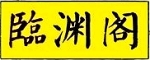
![[临渊阁]天地一家春](https://www.antiquekeeper.ca/wp-content/uploads/2023/03/cropped-Asian-Art-Wallpaper-Painting3-6-3.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