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刘静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明末清初是竹刻艺术最为精湛的阶段, 这种成就是与文人的介入分不开的。 当时有的文人、士大夫有着善饰书房之好, 如同仕女有装饰闺房之癖一样,他们喜欢用精致淡雅的雕刻小品把书房内的几案和多宝格装饰得十分讲究和别致。此风盛行, 使不少商贾也跻身于风雅之列,他们一边用外来的各种贵重硬木制造家具,装修隔扇,一边将搜集到的各式雅玩陈设在多宝格中,以示风雅。这种风气甚至随着士大夫的推崇而传入宫廷,使一些知名的雕刻能手由地方官推荐到皇宫服役,按照皇家指定的艺术风格进行创作。

据不完全统计,此时涉足雕刻领域的文人仕士多达140余人, 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人自己画稿,自行设计,亲自参加制作,有的甚至干脆以刻竹为终身职业。由于他们的鼓文弄墨,促刀弄笔,尤其是他们对竹的特殊爱好和推崇,一些制作精致、具有文人趣味的观赏品和各式文玩才日益兴盛,使之成为一项特种工艺,其艺术水平在很短的时间里便达到了顶峰。

当时的刻竹高手主要分布在江苏地区, 这些竹刻家们不仅能利用各种技巧,将竹简竹片制成文房用具,而且还能根据竹根的自然形态,独具匠心地制成新奇百状的人物、动物及瓜果、蔬菜。这些作品因雕刻技法和风格特征上的不同,当时就有濮派、 朱派之议,文人们根据地域,将这两种风格划分为金陵和嘉定两派。前者是以明代万历时期金陵人(今南京)濮仲谦的浅浮雕技法为主,这种技巧通常被称为“水磨”法;后者的特点则是以透空深浮雕、圆雕为主,创始人是明嘉靖时期的嘉定人(今上海嘉定县) 朱鹤。在朱氏祖孙三代中,艺术思路和艺术技法又一代胜似一代,而且师从三朱技艺的人非常多,只在嘉定一县,有名的竹刻能手就有67人。正是因为他们的创作和参与, 才使竹刻蔚然成风,嘉定一县也因竹刻而远近驰名。

明末清初时期传世的精湛作品很多,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明代濮仲谦的深浮雕 “松树”小壶、浅浮雕“竹枝”笔筒,朱鹤的深浮雕“松鹤”笔筒,朱小松的透雕“刘阮入天台”笔筒,朱三松的浅浮雕“仕女” 和“赤壁夜游”笔筒、圆雕“佛手”、“渔翁” 等。清代有吴之璠的浅浮雕“僧人”笔筒, 封锡爵、封锡禄圆雕的“晚菘”笔筒和“布袋僧”。还有许多未留下名款的“山水人物” 笔筒、留青“山水楼阁”笔筒及人物、动物、 瓜果式盒等。




乾隆丁酉新旾月御題。 后刻“三”、“隆”印二方。丁酉为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笔筒另一侧壁上又有“万历甲寅秋月三松作”款识。甲寅则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朱稚征雕刻的各种作品中,尤以仕女题材为多。在雕刻技法上,他多以浮雕为主,有时亦兼融毛雕、浅刻、深雕、留青、透雕等技巧。此笔筒利用多种技法将山石、苍松、花草和仕女的衣纹及神态举止刻画得恰到好处,刀法中见笔墨,树石皴法颇富画意。此件名家所制笔筒被收入宫禁,为皇帝所赏识。

从流派上讲,濮仲谦(1582年——清初)是金陵派的创始人,其作品通常以浅浮雕为土,喜欢用盘根错节的竹根或作竹,根据材料的自然形状和特征,精心构思设计,制成小巧玲珑、精美典雅的艺术品。《太平府志》 中说他“有巧思,以镂刻名世,一切犀玉竹皿器,经其手即占雅可爱”。他最擅长用刀很浅的浮雕技法,有人称这种刻法为“水磨器”,他用这种技法刻制扇骨、酒杯、笔筒、 臂搁之类,曾妙绝一时,受到世人的喜爱。 故宫收藏的一件“竹枝”笔筒,便是这种技法的代表之作。

“竹枝”笔筒,高14.6、口径6.9厘米, 呈棕红色。系以——节竹简从节处断开,留出所刻部位,其他竹筠直上直下全部刮去,现出竹肌,用局部浮雕法,刻出一梢垂竹。垂竹竹枝逐节歧分,直至梢尖,由粗而细向侧低伏,竹叶或向或背,或疏或密,形如雀爪, 组合分明。这件笔筒笔墨情韵极浓,由竹枝向、背低垂的姿势看,仿佛正经受着风雨的侵袭,生动自然,颇有雨意,俨然仿照李息斋双钩竹画本刻制而成。笔筒小巧精雅,有三分刻、七分磨之工,光泽莹润,抚触之下颇使观者爱不释手。从刻工上看,虽然是用刀很浅,不甚用力,但刻技超然,落刀简洁, 韵味无穷。有人说濮氏刻法不耐寻味,看来这只能说是门户之见。

濮仲谦与其他艺术家一样,是位一技多能的雕刻能手。他雕刻的另一件“松树小壶”,就是以深浮雕技法刻制的。小壶高 12.3、口径8.4、底径8.5厘米,用天然盘连的竹根枝干巧制而成。壶以松干为身,一根侧枝沿树身攀附而上,蟠屈成柄,断梗作流,壶盖巧雕成枝叶,曲折如钮,壶柄下隐刻楷书“仲谦”款。整件器物均由松枝松针联为一气,鳞片般的树干及纤细的松针,雕刻得极其细致写实,灵巧古朴兼而有之,既显得精巧雅致,又表现了松树的自然形态, 是件难得的竹刻精品,作为一级文物一直被故宫珍藏着。

嘉定派是以镂刻透雕及深浮雕为主, 在朱鹤、朱樱、朱稚征祖孙三代中,共同特点是能写擅画,以画刻竹。他们自行设计出不同的画稿图样,再用“立视体”和“通景式”方法,将图样转移到器物上,使作品布局结构严谨完整。同时,他们所设计刻制的纹饰也与众不同,是以南宗画法为本,揉入到北宗的雕刻中,又以深刻、高浮雕等北宗的雕刻法为体,刻制花鸟、人物、山水等图案。因此他们雕刻的花鸟纹饰有徐熙绘画的野逸风采,古仙佛像有吴道子的手笔,山水图纹又采用与夏风格。
朱氏祖孙三代中,初“为人博雅嗜古,而特工镂刻之技”的朱鹤,早年先学篆刻,后来旁及其他雕刻艺术,技艺既高超又受到时人的敬慕,是一位杰出的雕刻家。他的雕刻作品为世人珍重,被誉为嘉定派竹刻的创始人。其传世作品中,具有一件寓意“长寿”的“松鹤”笔筒。 17.8、口径8.9×14.9厘米,是用接近竹根处的一段老竹制成的。笔筒周身呈松树桩状,沿树身又并延伸一枝干,围抱巨干而生。主干上瘿节累累,苍鳞密布。枝干乔矫虬拿,松针茂盛,古意陵然。松间绘画仙鹤隔枝相对,有如嬉戏私语。在松皮卷脱露木处,题有阳文五行:“余至五,客于丁氏三清轩,识竹溪兄,笃于气谊之君子也,岁之十月,为甫熙伯先生八秩寿尊,作此奉祝。辛末七月朔日,松邻朱鹤。”朱鹤用熟练、精湛的刀法,采用技巧多种,重点突出了树身的变化。如密布的大小瘿结,凹凸孔陷的结疤,犹似火烫而出。古老多姿的松针,或三或五,重重叠叠,纤细若毫,那添加在松间的双鹤,又给静谧的树松增添了无限的生趣。这件珍品由著名收藏家储南强先生于50年代捐赠给南京博物院。


朱樱和朱稚征继承父祖以画入竹的刻竹之业,并深得其髓。朱樱号小松,工行草、 隶篆与诗画,博涉多能,他的诗风流洒落, 任意抒写,有自然之致,而他的画又长于气韵,有奇趣。朱稚征号三松,在继承中又有所发挥。他善画远山、澹石、丛竹、枯木等, 尤长画驴。他们父子成就十分突出,而三松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时就曾有“小松出而名掩松邻,三松出而名掩小松”之说。在雕刻中,父子俩的雕刻技法,除阴刻、 阳雕、立雕外,也作镂雕和留青阳文。他们均喜欢以仕女、文人的奇行异事、古道释人物和民间戏曲典故、传奇故事作题材,刻制笔筒、香筒、圆雕人物与动物。在设计和构图时,为了更好地利用笔筒的平面,他们用绘画中的留白技巧,以深刻技法安排纹饰中的松树、枫桐树等,又以浅浮雕技法表现空间上的远近,刻制山水人物,使器物上的纹饰饰如同一气哈成,连贯一体,非生作品硬之感。这种联体雕刻的代表作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小品。松刻制的“刘阮入天台”笔筒、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朱三松刻制的“窥简图”笔筒。两件笔筒丰富层次,画面收藏。因小松和三松的画长依气韵,使纹饰器形连成一气,透视效果全部。





小松、三松的圆雕技法也十分突出。他们刻绘古仙神像的手法独特,不但神情逼真,相貌奇古,衣纹装饰也有“吴带当风” 的韵味。北京故宫收藏的“竹根雕佛手”和 “竹根雕渔翁”,就是两件具有代表性的圆雕作品。竹根佛手高11、长15.5、宽5厘米。 呈立体并蒂折枝式,枝叶相连,姿态优美苍健,在枝端阴刻楷书“小松”款。佛手造型写实,上面棕点麻皮逼真,使用刀法十分精湛熟练,弯折掩映深浅多变,将佛手的英姿表现得淋漓尽致。竹根雕“渔翁”高13.5厘米,老翁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足蹬草履, 手提小筐,网得一尾鲜鱼正冒雨回转或前去换酒。老人一边躬腰前行,一边举起前臂用长袖抹着腮下的雨水。其脚筋显露,脚趾紧紧抓踩地面,表示着路面泥泞。在朱小松精湛的刀笔之下,渔翁被刻画得细致入微, 栩栩如生。尤其是那不顾雨水打湿面颊,努力前观,弯弯的前额及微微露出的笑容,充分表达出老翁欢快的心情。这两件作品,刀工浑厚,均给人以古拙朴实之感,体现了气韵生动、萧疏奇特的艺术风格。




器取用粗壮异形竹根,整治内腔后于外壁雕刻主题画面。整个设计以山间老松鳞皴巨干为主体,仙鹤、梅桩及竹叶灵芝附绕四周,奏刀深峻,洼隆浅深富有层次。雕镂松鳞、朽眼,将松树老干表现得十分自然;而松枝、仙鹤的雕刻手法细腻、鲜活与生机盎然,技法中运用了圆雕、透雕和高浮雕诸法,刀法与技艺极为娴熟。整器体量颇大,造型典雅别致,富有山林韵味。作为书斋中长物经年把玩,故而表面能呈现出琥珀色的光泽。 朱鹤号松隣(鄰),明竹刻名家,《竹人录》、《嘉定县志》中有录。其工书法、篆刻,精雕镂图绘之技,亦擅竹刻,为正德、嘉靖年间嘉定派竹刻的开山始祖。按“辛未”年当是穆宗隆庆五年(1571),此件竹雕为其晚年的一件代表性作品。



清代初期,继承朱氏雕刻技法的文人较多,其中成就超然的浮雕能手是吴之璠, 圆雕能手是封锡爵、封锡禄兄弟等。吴之璠(1644-1722年),字鲁珍,号东海道人。他工绘花鸟,善写行草书法,而且书风秀媚道劲。他师承朱三松,后来又将北魏的石雕技法融入到竹刻中,创造出一种稍稍突出地子的浅浮雕技法,即“减地浅浮雕”,也称 “薄地阳文”,这是一种以浅浮雕突出题材, 留空四周作为背景的新型雕刻法。这种浮雕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用深刻作高浮雕,深浅多层,高突处接近圆雕,低陷处则采用透雕技法;另一种是摹拟龙门石刻中的浅浮雕技艺,这种刻法介于朱氏高浮雕与浅浮雕之间,所刻的一事一物只占全部器皿的某一部分,其余部分则用去地法,刮至露出的肌理,任其光素。此种刻法,宾主、虚实分明,对比之下,素地可见到朴实的竹丝, 精镂细琢部分则肌润光泽。在竹刻技巧上, 吴之璠善于以景物来相互遮掩压叠。他刻的纹饰,层次分远近,在浅浮雕那有限的高度上,甚至在高低相间的表层上,都能给人以透视深度之感。因此,他所刻的人物、花鸟极为生动,流传至今的人物花鸟笔筒及行草秘搁,秀媚遒劲,为识者所珍。

在吴之璠众多传世作品中,最有名的有两件,一件是高浮雕技法刻制的黄杨木 “东山报捷”笔筒,一件是去地浅浮雕“僧人”笔筒。竹雕“僧人”笔筒,高17.3、口径9.4、底径9.2厘米。呈椭圆形,镶紫檀木口和底,下承四垂云足。图纹分两面,一面采用“薄地阳文”法,局部凹刻一荷杖僧人, 一面刻阴纹行书题诗一首。为了突出主题, 吴氏以其惯用的构图方式,在留白的地方刻上了一位光首赤足,手持佛珠串,肩扛棍杖前行的僧人。僧人面如满月,双耳垂肩, 咧嘴眯眼,笑容可掬,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十分逼真生动。作品刀法娴熟,功力超然。从笔筒布局及画面上看,浮雕僧人的纹饰虽然简练,但线条却十分婉转流畅,表现了“薄地阳文”雕刻技巧的风格和特征。

在嘉定圆雕竹刻中,号称鼎足的是封锡爵、封锡禄、封锡璋三兄弟。他们三人均工诗善画,精于竹根人物,《竹人录》中曾记载说:“竹根人物盛于封氏,而精于义侯, 其摹拟梵僧佛像,其踪异状,诡乖离奇,见者毛发竦立。至若采药仙翁、散花天女,则又轩轩霞举,超然有出尘之想。”由于他们刻竹技艺精绝,名声远播,当时地方官经常用他们的作品作为地方物产进贡朝廷,并推荐封锡禄、封锡璋进宫,在清宫养心殿造办处服务。

故宫收藏的一件封锡爵“晚菘”笔筒, 高16.2、口径13.4、底径7.8厘米,系量材度器,根据老竹根的形状,以白菜为题材, 采用圆雕、毛刻等技巧,将笔筒的外形刻成叶片重叠皱卷、根须溢出土面的晚菘之状。 刀法舒畅朗健,形态自然,宛如秋圃畦中所见。这种巧妙的赋予枯根以现实生命的艺术手法,没有精绝的镌刻技能是难以做到的。

“布袋僧”是封锡禄的作品,高7.2、底径10.4×8厘米。布袋僧袒胸露腹,盘膝曲肱,侧身斜首席地而坐,有5个小童分侍左右。可能一小童登攀抓抚,弄痒了弥勒,使他缩颈耸肩,双脚交错,眯眼纵鼻,咧开大嘴,一副开怀大笑的面容。阴刻的衣纹婉转、飘逸,线条自然流畅。整个作品刻工精妙,人物形象掌握准确,尤其是弥勒那两腮上肌肉露出的小坑,鼻、眼几乎挤成一堆, 表情刻画得惟妙惟肖。


那些没有名款的传世作品中,精绝的圆雕和深浅浮雕作品不在少数。如明代竹根雕“骑马人”,是以韩愈“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为题材,雕刻了一位顶风冒雪的骑马老人形象。老者头戴风帽,耸肩缩颈骑于马背之上;马的双眼圆瞪,四足叉开,双耳直竖,作立止不前状。配合着老人双手揣于长袖之中的神态,使人自然联想到在风雪中受阻的情形。作品刻工圆润细致,人物、马匹神态生动逼真。

圆雕竹刻“飞熊”, 高18.5、底径11×9厘米。飞熊双爪平举并微微上抬,扭身转首,双睛圆瞪,似在向前抓扑。其肩有双翅,背有长毛下披,腹部有宽条带似蛇腹,双耳又如哈巴狗,鼻如如意,双齿尖而下垂,神态奇异。这两件作品刻工圆润,既威严苍健,又生动活泼,代表了当时文人雕刻设计的倾向。

总之,明末清初的竹刻作品笔墨味很浓,其设计技巧虽然各异,但一般均清雅随意。在那些擅长文学、能书善画的文人雕刻家笔下,竹刻作品被赋予了深刻的文化内涵,并由此推动了竹刻艺术的迅速发展与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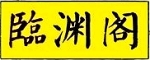
![[临渊阁]天地一家春](https://www.antiquekeeper.ca/wp-content/uploads/2023/04/BW-Erping-1a-17-6-1.jpg)
